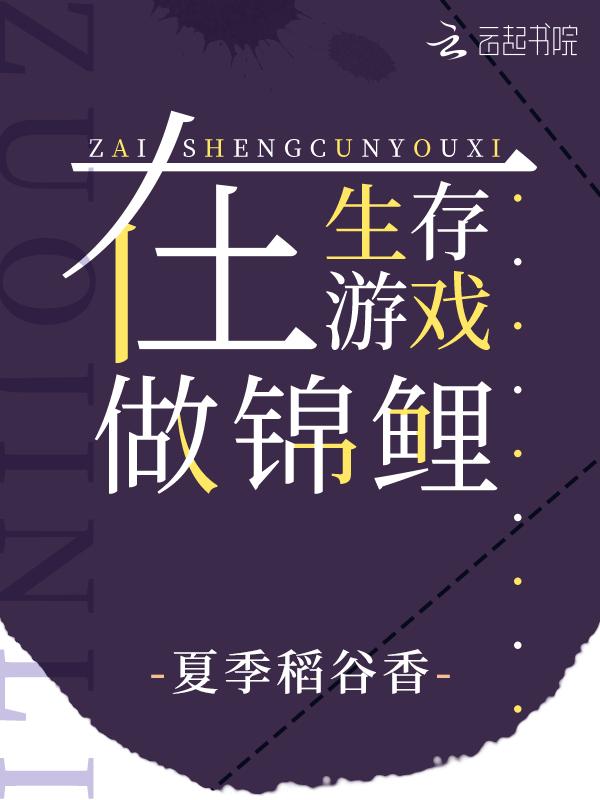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人在诸天,摆烂成帝 > 第六百六十五章禁区老鬼正义切割(第1页)
第六百六十五章禁区老鬼正义切割(第1页)
林仙盘坐于九重天上,宛若一尊古仙人,指尖荧光闪烁,凝结法印,施展出了禁忌神通。
时间之力如银练飞舞,每一道都带着岁月沧桑的厚重,仿佛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纪元,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意。
让旁观的至尊。。。
风穿过山谷的时候,带起了一串铃铛声。
不是金属的清脆,也不是玻璃的剔透,倒像是冰裂时那一瞬的轻响,又像老木门在夜里自己吱呀了一声。这声音没有源头,却无处不在。它不敲打耳膜,而是直接落在心上,像有人用指尖轻轻拨动了记忆里某根蒙尘的弦。
小镇的清晨向来安静,可今天的静法不一样。不是因为没人走动??孩子们照样背着书包蹦跳着上学,卖豆腐的老李推着车哼着小调,狗在巷口追自己的尾巴转圈??而是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被拉长了半拍,仿佛时间本身喝醉了酒,在门槛边多坐了一会儿。
少女站在院中晾围巾。
那条红底白点的围巾已经洗过许多次,颜色淡了些,边角也磨出了毛边,但她还是每天早晨把它摊在竹竿上,任风吹晒。她说:“它记得很多人。”
林仙曾问:“一条围巾能记得什么?”
她答:“记得手的温度,记得等人的夜晚,记得某个冬天,有个人把它围在一个发抖的孩子脖子上,然后笑着说‘没事啦’。”
今天,围巾展开的瞬间,忽然飘了起来。
不是被风吹起的那种飘,是它自己缓缓离杆,像一片叶子逆着重力上升。阳光穿过布料,显出细密针脚间流动的微光,那些原本看不见的线迹此刻竟如星图般闪烁,勾勒出某种古老的符号结构??七组环形纹路,中心一点空白。
“第七瓣花……”林仙站在门口,终端早已报废,她只能凭直觉记录,“不是开了,是反向闭合了。信息回流。”
她低头看着掌心。那里不知何时浮现出一道极淡的印痕,形状像是一把钥匙的轮廓,边缘模糊,似由雾凝成。她试着握拳,印痕却不消失,反而渗入皮肤,化作一股温热流向心脏。
与此同时,宇宙深处传来一声“叹息”。
不是悲伤的叹,也不是疲惫的呼气,而是一种确认般的吐纳,如同旅人终于抵达目的地后,轻轻放下行囊的声音。银河旋臂边缘的一颗死寂行星突然亮起,表面浮现出与围巾上相同的纹路,一圈接一圈地扩散,持续了整整三十三分钟,随后归于沉寂。
没有人观测到这一幕。
或者说,所有人都“知道”了,但没人“看见”。
就像你不会注意到呼吸的存在,除非它突然停止。
陈砚坐在摇椅上啃西瓜。
瓜皮绿得发亮,他咬一口就甩一瓣到墙角,堆得像座小山。他的牙齿不太整齐,吃东西总带着点孩子气的笨拙。路过的小孩笑他:“爷爷吃得像个猴子!”
他头也不抬:“猴子还知道挑甜的呢,你懂啥?”
没人发现,他每咽下一口瓜肉,舌尖都会尝到一丝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滋味??那是千年前某个沙漠部落祭祀时酿的果酒,是两百年后一颗漂泊行星上最后一名人类画家临终前喝的凉茶,是此刻正穿越虫洞的探险家背包里那块融化的巧克力。
记忆的碎片,顺着味觉涌来。
他没说话,只是把最后一口瓜含得久了些,直到甜味褪去,只剩水分滑下喉咙。然后他说:“原来西瓜也能当镜子使。”
少女收回飘在空中的围巾,轻轻叠好,放进木箱底层。箱子不大,里面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旧物:一只断了发条的闹钟、半本烧焦的日记、一枚生锈的硬币、还有几张泛黄的照片,上面的人影全都模糊不清,唯独背景里的问题树清晰如昨。
“他们在找我们。”她说。
“谁?”林仙问。
“后来的人。”她指着窗外远处的山坡,“他们立碑,录音,建纪念馆……可他们忘了,我们从来就没‘离开’过。我们只是变成了‘背景音’。”
林仙沉默片刻,忽然笑了:“所以现在,我们是世界的BGM?”
“不止。”少女摇头,“我们是那个让你在加班到凌晨时突然停下来说‘算了,明天再说吧’的念头;是我们让你在吵架中途看见窗外下雨,就顺手把伞递给陌生人;是我们让你在面对选择时,哪怕知道会错,也愿意试一次。”
她顿了顿,望着天边渐起的云:“真正的共情,不是教会别人怎么哭,而是让他们明白??你可以不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