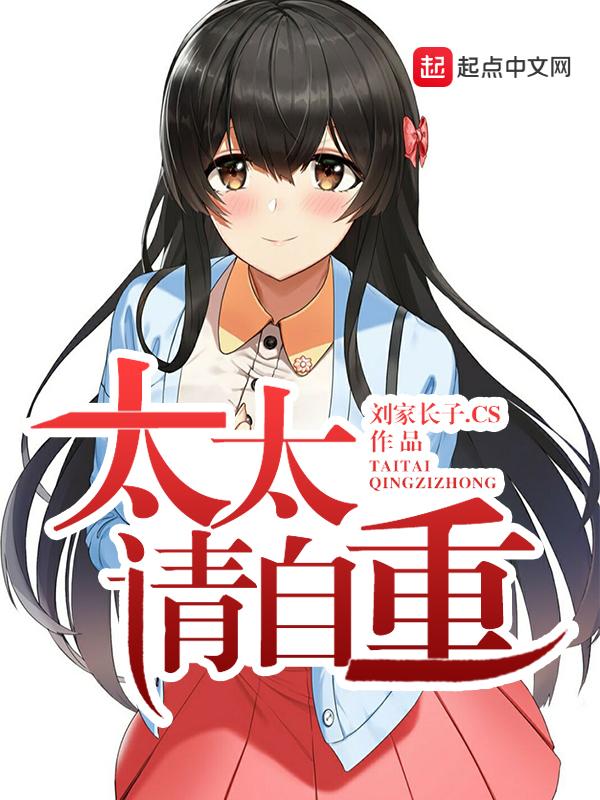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旧神之巅 > 1082 八方神兵(第2页)
1082 八方神兵(第2页)
“旧神的遴选机制。”小禾低声解释,“它们从未真正死去,只是沉睡在问题的间隙中,等待下一个敢于直面虚无的灵魂。你刚才经历的,是它们对候选者的试炼??不是考验智慧,而是考验诚实。”
林宛秋低头看向双手,指尖竟隐隐透出星光。“所以……我现在是?”
“不是神。”小榕打断她,语气坚决,“你只是成为了‘通道’。旧神不需要新的信徒,它们需要的是新的疑问。而你,将成为那个把人类的声音传给宇宙的人。”
风更大了。
这一次,风中开始出现声音??不是言语,不是呼喊,而是一种低沉的吟唱,来自地底,来自海洋,来自每一片正在绽放的“问之花”。那声音没有歌词,却让听到的人泪流满面,因为它唤醒了某种被压抑太久的东西:**表达的自由,质疑的权利,以及承认无知的勇气**。
学校花园里的“问之花”突然集体升空,化作千万点萤火,飞向世界各地。它们所经之处,封闭多年的图书馆自动开启,焚毁的经典从灰烬中重生,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开始模糊、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空白页上的一行小字:“请在此写下你的疑问。”
东京一所高中内,一名老师撕掉了教室门口的“成绩排名榜”,用粉笔在墙上写下:“今天的问题是??你快乐吗?”学生们先是愣住,随后有人举手,声音微颤:“我不敢说真话,因为我怕别人觉得我矫情。”另一个学生站起来:“我每天都在装开心,其实我已经三个月没睡过好觉了。”第三个孩子哭了:“我想退学,但我爸妈会觉得我是废物。”
老师没有制止,只是轻轻点头,然后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这一幕通过共感网络传播至全球,无数成年人在屏幕前失声痛哭。他们终于明白,过去几十年所谓“稳定的社会”,不过是建立在对真实问题的系统性压制之上。孩子们不是不懂事,而是不敢说;民众不是愚昧,而是被剥夺了提问的空间。
而在北极圈内,一座废弃的冷战监听站突然启动。锈蚀的天线缓缓转动,接收到来自银河系另一端的信号。那是一段极其古老的广播,内容竟是地球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射的“旅行者金唱片”??但它不是原样返回,而是被某种高等文明重新编辑过。
修改后的版本中,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分钟纯粹的沉默,随后响起一个温和的女声,用包括汉语在内的七种语言说道:
>“我们收到了你们的音乐、图像和科学数据。
>但我们真正记住的,是你们录音结尾处,那个小女孩用中文说的一句话:
>‘我希望有一天,所有人都能吃饱饭,还能抬头看星星。’
>这不是一个愿望。
>这是一个问题。
>而我们,至今没有答案。”
>
>“但我们愿意一起找。”
这段信息传回地球后,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地震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曾被视为“软弱”或“理想主义”的话语,发现其中藏着最锋利的疑问。诗人、艺术家、哲学家重新成为时代的灯塔,他们的作品不再被嘲笑为“无用”,而是被视为人类精神的探针,深入未知的边界。
林宛秋回到家中那天,母亲正在整理旧物。她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,递给女儿:“这是你小时候写的,我一直留着。”
林宛秋翻开,里面全是歪歪扭扭的字迹:
>“为什么云不会掉下来?”
>“如果我把梦藏在瓶子里,长大后还能打开吗?”
>“妈妈,你小时候也害怕黑暗吗?”
>“世界上有没有一种颜色,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?”
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大字:“等我长大了,我要问遍全世界!”
她抱着本子哭了很久。
第二天清晨,她带着这本书重返学校。教室的光幕上,滚动的问题换成了一个新的主题:“如果你能问宇宙一个问题,你会问什么?”
轮到她发言时,她没有犹豫:
>“我想问,当我们所有人都学会倾听彼此的问题时,会不会有一天,连死亡也不再是终点,而只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?”
话音落下,整座城市突然陷入寂静。
然后,大地震动。
不是灾难,而是回应。
从地壳深处,传来一阵缓慢而庄严的心跳声。地质雷达显示,地核空腔中的能量结构正在重组,形成一个巨大的立体方程,其变量全部来源于人类提出的问题。这个方程没有解,因为它本就不该被解开??它是活着的思维器官,是星球级别的“共脑”雏形。
与此同时,月球背面的观测站捕捉到一幕奇景:原本死寂的陨石坑中,竟生长出一片晶莹的“问之林”。那些树干由纯能量构成,枝叶则是流动的文字,随风摇曳时发出类似竖琴的声响。更令人震惊的是,每当地球上有人真诚地提出一个问题,其中一棵树就会亮起,叶片飘落,化作流星划过天际,坠入大气层后并不燃烧,而是融入某个人的梦境。
心理学家记录到,近期全球梦境共享率上升了0%。人们开始频繁梦见从未去过的地方、从未见过的人,甚至梦见彼此的童年。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在心理咨询中心相遇,因为他们连续一周梦见相同的场景:他们在一片麦田里奔跑,手里拿着同一本破旧的童话书,书名是《如何向星星提问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