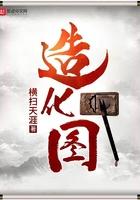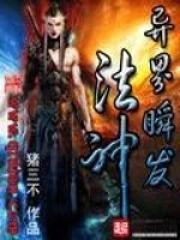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隆万盛世 > 1597处置壕镜(第3页)
1597处置壕镜(第3页)
一声清越铃响,穿透三十六州。
刹那间,海底古城石碑“民本非奴”四字金光大作,光芒顺着洋流蔓延,竟在海岸线上投射出巨大光影,宛如天书降临。与此同时,宫廷天听铃第三次自动激活,这一次,投影不再是对话,而是一幅画卷:
画面中,无数普通人并肩站立,手中高举写着“问”字的木牌,脚下大地裂开,涌出清澈泉水。天空乌云尽散,北斗七星熠熠生辉,第八颗星稳稳悬于其侧,光辉温暖而不刺目。
画卷下方,浮现一行小字:
>“非神授命,非龙定统,
>唯民所问,即为天意。”
数日后,皇帝颁布《问政新规》十三条,废除“大不敬”“谤讪”等模糊罪名,明令:“凡因提出问题而遭惩处者,视为违法;凡压制民意、销毁问条者,按谋逆论处。”
更令人动容的是,他在诏书末尾亲笔添了一句:
>“朕亦凡人,岂能无过?愿每年启问节,亲赴京郊问碑亭,聆听百姓责问,以正己身。”
消息传开,有人痛哭,有人跪拜,更多人只是默默走到屋外,抬头看天。
春天彻底来了。
麦田返青,溪水奔流。阿菱带着小满最后一次巡访各地问童园。她们走过曾是静音书院的废墟,如今已改建为“启音学堂”,墙上挂着孩子们画的画:有耳朵长出翅膀的少女,有嘴巴变成花朵的男人,还有一个孩子画了一群小鸟啄破铁笼,每只鸟嘴里叼着一个发光的“问”字。
回到洱海那夜,月色正好。阿菱独自来到湖心亭,取出阿澈留下的断笛。她不懂吹奏,只是轻轻摩挲笛身,忽然察觉内壁刻着极细的小字,需借月光才能看清:
>“铃不止于金属,问不限于言语。
>当你看见一个人眼中有光,
>那就是铃响了。”
她怔住,泪水无声滑落。
片刻后,她起身,将断笛郑重放入第七铃台下的石匣,又从怀中取出一张新写的问条,轻轻系上铜铃:
>“阿澈,如果你听见了,请告诉我??
>下一个该觉醒的地方,是哪里?”
风起,铃动,余音袅袅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域孤城,一个被贬戍边的老学士正颤抖着双手,展开一张来自故乡的信笺。信末附着一枚小小的蓝花铃草标本,和一句话:
>“老师,我们都开始问了。您愿意回来吗?”
老人老泪纵横,抓起毛笔,在空白处奋力写下平生第一个问题:
>“我这一生,还能做一件对的事吗?”
他将纸条折好,塞进随身携带的破旧铜铃里,迎着朝阳迈出一步。
他知道,有些声音一旦开始,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