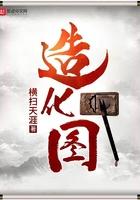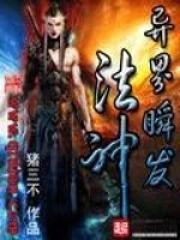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隆万盛世 > 1597处置壕镜(第1页)
1597处置壕镜(第1页)
虽说魏广德有把握控制阁议的结果,但是该有的程序还是要走。
就比如明日上奏,他也不可能直接就把今天和申时行说的三个人,堂而皇之就写进奏疏里。
只能是以内阁缺人的理由,请求皇帝增补阁臣。
。。。
南岭的春来得迟,山雾如纱,缠绕着回音谷的每一块青石。阿菱站在第七铃台前,指尖轻抚那枚嵌有双频晶片的铜铃,它静默地悬在风中,仿佛仍在等待一个未完成的回应。小满蹲在不远处,教孩子们用竹片和铜丝制铃,叮叮当当的声响像碎玉落盘,惊起林间几只山雀。
“姐姐,你说阿澈哥哥是不是变成了风?”一个小女孩仰头问,手里攥着半成品的小铃,眼睛亮得像晨露。
阿菱没有立刻回答。她抬头望向山谷尽头??那里曾是深井所在,如今已被一圈低矮石墙围起,墙上刻满了新补的名字。有人每日来添一笔,有人默默献上一盏油灯。她说:“他不是风,也不是光。他是第一个听见沉默有多重的人,所以走得太远,太早。”
小满走过来,递给她一碗热茶。“昨夜洱海传来消息,‘问史局’从影阁旧档里挖出一份密录,记载了三百年前一场‘万童噤声祭’。”她声音压低,“当年永乐帝为镇压民间异论,命影阁选九百童男童女,以‘定音咒’封其喉脉,使终生不能言不许问,谓之‘净口献礼’。这些人后来全被埋入皇陵地基之下,作为‘镇魂桩’。”
阿菱的手微微一颤,茶面荡开涟漪。“难怪……南岭古庙倒铃上的符文,我后来辨认出来,竟是用孩童指血画的。”
两人相视无言。远处的孩子们仍在欢笑,摇着手中的小铃,一声声清脆划破晨雾。可这笑声越响,她们心中越沉??因为知道,每一记铃音背后,都曾有过无数被掐灭的声音。
三天后,京城快马加急送来诏书:皇帝亲笔御批,《启问节》正式载入国典,并下令在全国各县设立“问碑亭”,凡百姓所提民生之问,须由地方官当场诵读、限期答复。若三月无果,可直奏中枢,不得阻拦。
与此同时,沈知意主持的记忆修复组取得突破。他们发现,那些曾在乌蒙矿场遭受“失语刑”的孩子,脑中并非没有记忆,而是被一种特殊的声波频率锁住了语言中枢。通过模拟“七铃共振”节奏,辅以手语与图画引导,已有十七名患儿重新开口说话。
其中一名十岁男孩,在恢复意识当晚写下第一句话:“我想念妈妈的味道。”
第二天,他又问:“为什么坏人能穿官服?”
这句话被传至宫城东墙,刻入“问影碑廊”第三十七列。当晚,天听铃再度微震,投影出一段模糊影像:一座幽暗殿堂内,数名黑袍人围坐圆桌,中央悬浮一枚漆黑铃铛,铃身布满裂纹,却仍缓缓震动,发出几乎不可闻的低鸣。
阿菱看到影像时,心头猛然一紧。她立即调取《触音全谱》残卷对照,终于在一页焦黄纸页上找到记载:
>“黑铃者,逆响之器也。取怨气为薪,以绝望为弦,可反向吞噬万民之声,令问者自疑,答者失信。昔年仁宗毁其形,然心火未灭,潜藏于权欲深处。”
她立刻命人封锁消息,同时启动“破影计划”第二阶段:在全国八十一座主要问铃台布设“清音结界”,以正向共振抵消潜在的负面声波干扰。
然而,风暴并未停歇。
腊月初七,广西“问殇园”守园老仆突然失踪。次日清晨,人们发现园中主碑被人泼洒黑色油膏,碑面浮现诡异文字:
>“多言者乱,妄问者亡。
>静者生,鸣者死。”
更令人骇然的是,当晚各地信鸽驿站接连报告:一批伪造的“问条”混入传递系统,内容均为自我否定式的呓语:
>“我不该问。”
>“没人会听。”
>“闭嘴才是活路。”
这些纸条竟带有微弱磁性,能吸附于真问条之上,久而久之,竟使部分共鸣阵列产生杂音,湖心蓝光一度转为暗红。
阿菱连夜召集沈知意、小满及几位核心信使商议。烛火摇曳中,沈知意沉声道:“这不是简单的破坏,而是一场‘认知战’。有人想让我们自己放弃提问??当怀疑扎根心底,比刀剑更致命。”
小满盯着地图上那几处异常节点,忽然道:“你们看,这些伪造问条出现的地方,恰好连成一条线,指向……西山皇家乐坊旧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