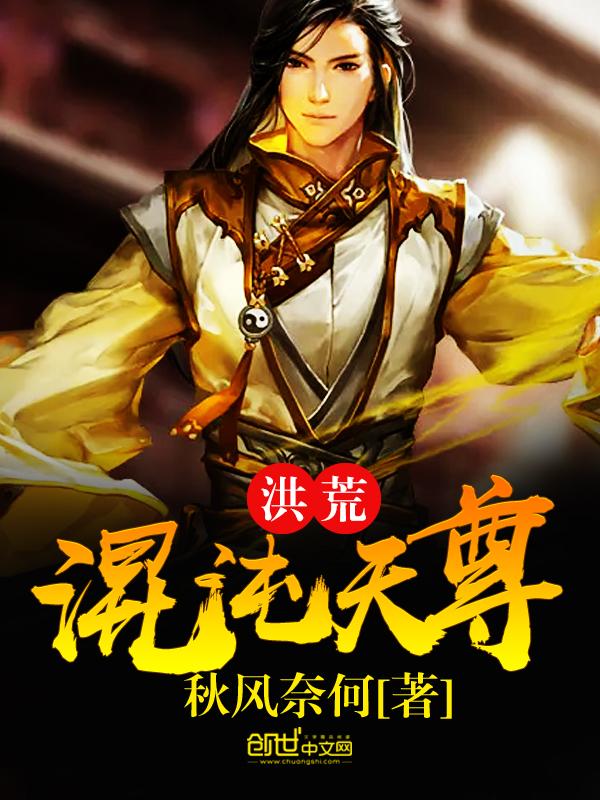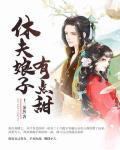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穿越之夫子科举日常 > 100110(第47页)
100110(第47页)
而走出国子监的爷孙两人,正进行着一场尴尬的沉默。
林鸣息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也不说话,但他握着马车边缘,突然道:“爷爷,我从小就一直听你的话,你说什么是对,我便觉得什么是对,你说什么是错,我便觉得什么是错。”
“可现在,我还是觉得周会元与我说的话,是对的。”
“周会元告诉我,我应该明白我是在为什么读书,在为什么求取学问。爷爷,你能告诉我,我为什么在读书吗?仅仅是因为我在读书上,很有天赋?”
“……”林范集登上马车,刚刚掀帘便停下,他并未回头,只道:“求道便是求道,哪有那么多为什么。古往今来,所有读书人不都是从蒙学便开始读书,然后一路科举,考出功名,卖与帝王家?这条路子,从未变过,以后也不会改变。”
“爷爷曾获取天下名声,被所有读书人敬仰,现在不还是每日上朝,下朝,整日和文书奏折,政务为伴。”
林鸣息跟着登上马车,帘幕放下,遮住小少年的声音,“爷爷,鸣息确实许久不见爷爷的墨宝了……爷爷,你有多久没有写文章了?”
林范集慢慢闭上眼,“记不得了……好像从穿上这身二品朝服时,就没再执笔过。”
马车晃晃悠悠前行,爷孙俩也不再说话。
不过,各人有各人的心事。
第110章
参加殿试的贡生一共有三百人,但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贡生,在殿试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,弄污了卷子,或者干脆就没写完,又或者胡写瞎写。
这些贡生,只能算同进士,将来最好的结果便是领一个小官职,外派到其他地方,慢慢熬资历。
而剩下的卷子,则需要好好审看一番。
不多,也就一百五十多份。
敬宣帝钦点了林范集,张翰林,刘大人,外加其他几位正二品的官员一同挑灯夜战。
还有另外专门帮他们分类卷子的同考官,大家互帮互助,定能在规定时间内判出名次。
所有人齐聚宝嘉殿,同考官们闷不做声,只一下又一下分着手上的卷子。
而他们之外,那几位主考的大人,时不时便为一份卷子争吵不休,吵到气头上,吹胡子瞪眼都是常有的事。
到这时,敬宣帝便端着温热的茶杯,给这几个上头的老家伙们看茶,让他们不要吵,不要闹,好好看卷子才是。
同考官们怎么也想不到,原来当大臣们吵架时,陛下才是那个和事佬和定心丸。
看在陛下的面子上,这些大人们咽下自己的想法,冷眼继续判卷。
可安宁不到几刻钟,他们又会因为另一份卷子吵起来。
几个晚上过去,同考官们竟然已经习惯这样的场景。
只有几种卷子,这些大臣们不吵。
一是,写的一般,他们只需要一个眼神,便能确定该名贡生应该排在多少名。
一种是写的极好,这样的卷子,不需要多加考虑便能放到甲等里。
贡生们的卷子虽然是按照座位收录的,可还是要打乱顺序,并封号。
只是到了殿试这里,不需要再额外誊抄一份,所以看到那熟悉的文章风格和笔记,熟悉的人,一眼便能认出这是哪位贡生的卷子。
张翰林拿着林鸣息的卷子,捻须点头,“老林啊,你这乖孙确实不错,文风稳健,笔锋犀利,颇有你当年的风采。”
“还差得远,还差得远。”林范集面对这样直白的夸赞,笑着谦虚。
这场殿试里,虽有林范集的乖孙,他倒是想避嫌,但林范集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大儒,他若是避了嫌,再难有第二个如他一般不与氏族有关系,又名声尽显的大儒来撑场面。
再说了,林范集那乖孙,满京城有谁不认识,三岁识千文,五岁背诗词,简直天生就是为了读书来的。
这样一名学子,不说林范集了,就是旁的人来判,那也是前三名的排名。
林范集这个亲爷爷何苦去避嫌。
他们这一行人,从下了朝便聚在一起判卷。
现在打更三声,他们才看过去一半。
刘大人揉揉眼睛,掏出怀中的清眼液,打开小葫芦,用洁净的锦帕蘸取一些,擦到眼睛上,缓解疲劳。
张翰林也忍不住掏出太医院送来的丹药,放入口中。
他们这些人都上了年纪,熬不动了,做这种耗费心力的事情,就得靠药物来维持身体健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