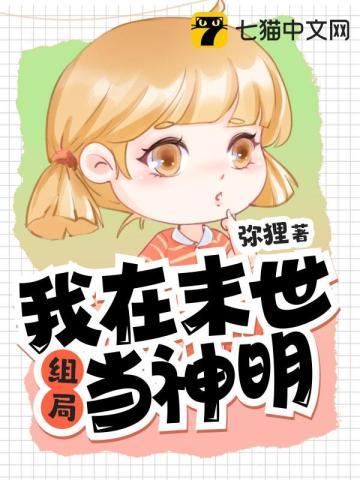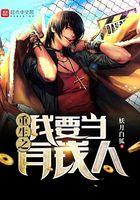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解春衫 > 第137章 她必须得死(第2页)
第137章 她必须得死(第2页)
“归雁,去库房翻一翻,母亲留下的那件藕荷色绣兰褙子还在不在。”
“在是还在……可那是旧衣了,颜色又素,怕衬不起场面。”
“正因素净,才显底气。”戴缨转身凝视铜镜,“我要穿它去。让所有人看看,什么叫‘贫而不卑,贱而不谄’。”
当晚,戴缨独坐灯下,提笔写下几行字:
>“若世道不容我直行,则我便曲中求全;
>若众人皆欲我低头,则我偏要挺颈而立。
>不争宠,不惧谤,不动于心,不乱于形。
>待春风过境,自有花开满庭。”
写罢焚之,灰烬落入茶盏,沉底如泥。
翌日清晨,戴缨照常教书,陪陆溪儿习字诵读。午后则闭门不出,研读《礼记?内则》,细细揣摩贵族女子言行尺度。她知道,在谢府那等场合,一字出口、一步前行,皆可能成为攻讦把柄。唯有滴水不漏,方能全身而退。
第三日,陆铭川遣人送来一只锦盒,内藏一对玉镯,通体莹润,雕工精细,底部刻有极小的“陆”字印痕。附信寥寥数字:“旧物归主,勿却。”
戴缨握着玉镯良久,指尖轻抚那枚印记。这是陆家嫡系女子成年时才会佩戴的信物,象征身份与认可。陆铭川此举,是在公开承认她的地位?还是另有所图?
她不敢轻易戴上,唯恐招嫉惹祸,却也不敢退还,以免被视为拒斥陆家恩典。
最终,她将玉镯收入妆匣最底层,覆以一方红绸,仿佛埋下一枚尚未引爆的火种。
第五日夜里,暴雨再临。一道惊雷劈裂天幕,照亮整个陆府。戴缨猛然惊醒,听见窗外有人低声呼唤:“戴娘子!戴娘子快开门!”
她披衣起身,归雁颤抖着打开门,只见一名浑身湿透的小厮跪在阶前,手中紧抱一只油纸包好的信封。
“小的是谢府药童……昨日奉命销毁安神香灰,但我偷偷留下少许样本……三爷救过我家老母性命,我不能昧良心……”他声音发抖,“谢元朗昨夜密会谢管家,说要在春宴当日,在饮食中混入迷药,让您当众失态,诬陷您勾引三爷、意图夺权……他还说……若事成,便许我全家脱籍为民……”
戴缨接过油纸包,入手微凉,里头确有一小撮灰色粉末。她立即命归雁取密封瓷瓶收好,又赏了小厮银钱,叮嘱他速速离开,不得透露半句。
待人走后,她坐在灯下,久久未动。
风暴终于逼近眼前。
她原以为谢家只会造谣中伤,却不料竟敢公然下药构陷。若非这名药童良知未泯,她将在众目睽睽之下丑态百出,甚至可能被当场逐出陆府,永世不得翻身。
“他们不怕报应吗?”归雁泣道。
“怕?”戴缨冷笑,“权力面前,哪有什么报应?只有成败。”
她站起身,走到书案前,铺开一张素笺,提笔疾书:
>“大人:
>春宴将至,恐有奸人作祟。
>昨夜得密报,谢氏拟于席间用药陷害,毁我清誉,乱陆家纲纪。
>样本已存,可验毒性。
>若大人不信,三日后城南济仁堂午时诊脉之人中,必有一妇人突发昏厥,症状与崇哥儿相似,乃同源之药所致。
>敬请留意。
>??戴氏谨禀”
信毕,她吹干墨迹,密封入函,交予心腹仆妇,命其黎明即送往陆铭章书房。
做完这一切,她才躺回床上,闭目养神。窗外雨声渐歇,鸡鸣初起,新的一天悄然降临。
第七日,春宴如期举行。
谢府张灯结彩,宾客盈门。戴缨乘一辆朴素青帷车抵达门前,身着母亲遗下的藕荷色褙子,发间仅插一支白玉兰簪,素净得近乎寒酸,却又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雅致。
谢珍远远望见,嘴角微扬:“瞧瞧,这不是咱们的‘贞女’来了?穿得跟奔丧似的,莫不是想博同情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