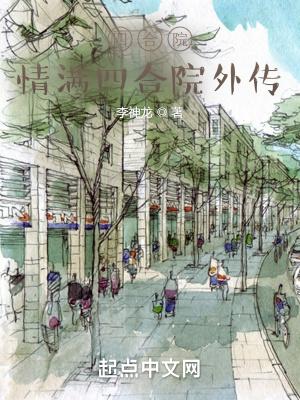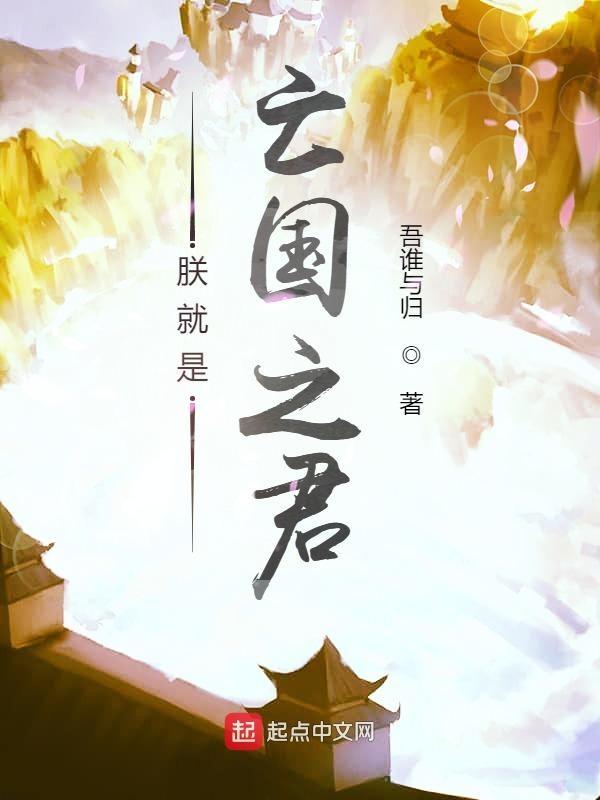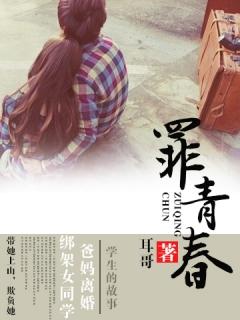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我的白月光是受害者 > 为什么还没来(第1页)
为什么还没来(第1页)
等待的时间好像突然变得黏稠而缓慢。
沈知秋依旧按部就班地吃饭、睡觉、待在角落。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怀里那只米黄色的小羊玩偶成了她沉默世界里最喧闹的存在。
她几乎时时刻刻都抱着它,或者把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星期一,她抱着小羊坐在老地方,手指无意识地卷着它背上的绒毛。阳光的位置和上周六差不多,可身边空荡荡的。
她低下头,用只有小羊能听到的音量,含糊地练习着那个词:“下……下周六……”声音干巴巴的,不如那天说出口时清晰。
她有点懊恼地抿住嘴。
星期二,阿姨分发水果时叫了另一个小女孩“秋秋”。沈知秋正摸着小羊的耳朵,闻言动作一顿。
她忽然意识到,那个人,那个每周都来的人,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。
当然,那个人也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她们之间,除了那些故事和糖果,除了这只小羊,什么都没有,连一个称呼都没有。
这个发现让她心里莫名地空了一块。
星期三夜里,她抱着小羊躺在床上,窗外的路灯光冷冷地照进来。
她想起那个人说的萤火虫,“因为它们的光,是为了找到彼此”。
名字,是不是也像一种光?有了名字,是不是就能在很多人里,准确地找到那一个?
她把这个想法紧紧搂在怀里,像搂着一个温暖的秘密。
星期四,她在院子里看到两只麻雀在打架,叽叽喳喳的。
她下意识地转过头,想对身边说一句“看,它们吵架了”。
身边只有空气。她愣在那里,抱着小羊的手臂紧了紧。
原来,她已经开始习惯,把心里那些细小的念头,变成声音,说给那个人听了吗?
星期五,一种清晰的、带着焦灼的期待感,像慢慢烧开的水,在她心底咕嘟咕嘟地冒泡。
她反复回想着那个人点头说“会来的”时的样子。
是真的吗?会不会是骗她的?像以前小文那样?这个念头让她害怕地缩了缩。
但怀里小羊柔软的触感,又奇异地安抚了她。
小羊是真的,那个人给的糖和故事也是真的。
她开始更努力地“练习”。
她对着小羊黑色的玻璃眼珠,小声地、一遍遍地重复:
“我……叫沈知秋。”
“你……叫什么?”
有时候,她会把顺序调换过来:
“你……叫什么?”
“我……叫沈知秋。”
句子很短,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沉重的石磨里艰难碾出来的。她会因为一个音发得不够清楚而皱起眉头,然后更加小声地再试一次。
这是她给自己布置的一个重要的、秘密的任务。
她甚至想象了一下说出这句话的场景。是在放下糖果的时候?还是在讲故事之前?或者……在离开的时候?每一种设想都让她心跳加速。
她怕自己临阵退缩,怕声音太小对方听不见,怕……怕那个人其实并不在乎她叫什么。
但那种想要知道对方名字的渴望,想要让对方也知道自己名字的冲动,像一颗顽强的小芽,顶开了所有犹豫的碎石。
她决定了,下周六,一定要问。
她要告诉那个人,自己是“沈知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