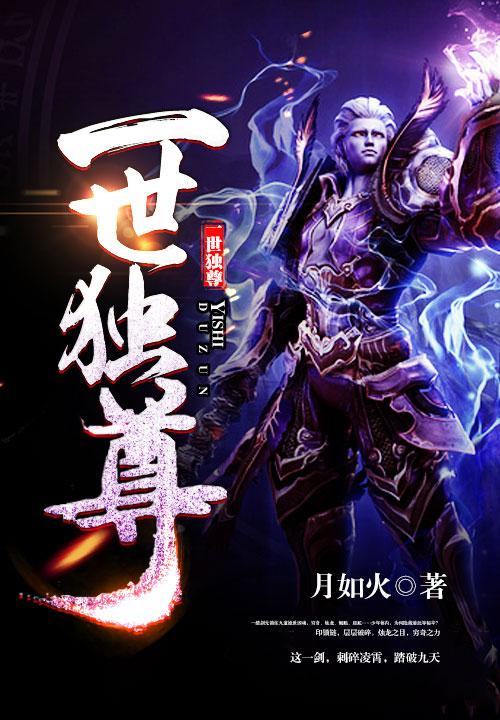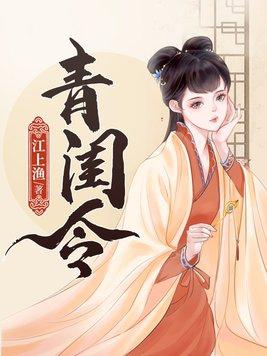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本官娘子就是妖 > 第一百五十六章 未来的天策上将(第1页)
第一百五十六章 未来的天策上将(第1页)
“??嘛?呢?叭?咪???”
面对来势汹汹的白素贞,白衣僧人面色不改,脚步轻盈,身若飞羽,从容自若地躲过白乙剑来,尔后神情专注,念动咒语,刹那间,金光万丈,虚空之中,神佛虚影涌动,浩大一掌拍向白。。。
夜风拂过江面,河灯摇曳如泪眼。那一点微光在水波中缓缓漂远,映着戒色沉静的脸。他蹲在岸边,指尖轻触水面,涟漪一圈圈扩散,仿佛要将过往的恩怨也荡开去。可他知道,有些东西,是水流带不走的。
母亲如今住在村东头那间低矮的茅屋里,每日清晨诵《心经》,午后纺纱,黄昏时坐在门槛上望着夕阳出神。她已渐渐恢复了些气色,白发间竟也生出了几缕青丝,只是眼神依旧空茫,像是总在等一个人归来??那个永远回不来的林砚之。
戒色不敢告诉她真相全貌。只说父亲遭奸人所害,仇已报,家难平。苏婉清听了,只是轻轻点头,喃喃道:“他临死前……可曾念我?”
戒色哽住,良久才答:“念了,娘亲,他至死都唤着您的名字。”
那是谎话。但他宁愿让她心中留一缕温存,也不愿她再知那血淋淋的结局??她的夫君被推入江心,连尸骨都未曾寻回。
而秀妍呢?
他不知她是否拆开了那封信。也不知她是否曾在月下反复摩挲那半块玉佩,对着拼合的龙纹怔怔落泪。他曾托山中采药人悄悄打探消息,得知她未再嫁,独自守着林府旧宅,闭门谢客,只每逢初一十五,必赴寺中焚香,跪在大雄宝殿前久久不起。
“她问起你。”采药人说,“问我见过一个穿粗布衣裳、眉间有赤痣的男子没有。我说没见过。她就哭了,说梦见有人站在江边点灯,背影极像故人。”
戒色听罢,一夜未眠。
他原以为斩断情缘便可心如止水,却不知人心一旦动过真情,便如刀刻石痕,纵使掩埋千年,风雨一冲,依旧清晰可见。他日日在田间劳作,挥锄劈柴,汗水浸透衣衫,只为让身体疲惫到无暇思虑。可每当夜深人静,秀妍的笑靥、她说话时低垂的眼睫、她递来玉佩时指尖的微颤,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更令他不安的是,自林正南死后,城中风云渐起。
先是林府账册失窃,接着几位与林正南过往甚密的官员接连暴毙,死状诡异,皆为七日后突发心疾,口吐白沫,四肢蜷缩如弓。江湖传言四起,说是“文渊阁”后人归来,以毒复仇,清算旧账。更有甚者言之凿凿,称见一黑袍女子夜行于官邸之间,袖中藏符,目如寒星,正是当年失踪的林家姑母。
戒色心中雪亮:姑姑并未罢手。
那一日暴雨倾盆,电闪雷鸣,姑姑突然出现在山村外的破庙里,浑身湿透,左臂缠着渗血的布条。她一脚踢开门板,冷声道:“你还在这儿种地?天下要变了!”
戒色扶母亲安置妥当后才赶来相见。他递上干布与热汤,低声问:“谁又死了?”
“巡按御史赵崇文,兵部主事周怀安。”姑姑冷笑,“这两个伪君子,当年明知你父冤死,却因受林贼提拔,助纣为虐,篡改卷宗,封锁江案。如今一个个都该偿命。”
“你用了‘牵机引’?”
“不止。”她从怀中取出一本泛黄册子,“这是我在林府密室找到的‘换籍录’,记录了当年如何伪造身份、顶替功名、勾结权贵的全过程。上面的名字,一个都逃不掉。”
戒色翻开册页,手指微微发抖。一页页看去,赫然列着数十个官名,其中竟有当朝丞相府的门客、刑部侍郎、甚至宫中内监总管。这些人,或知情不报,或参与构陷,或分得赃银。他们共同编织了一张巨网,将真相牢牢压在江底十四年。
“你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?”他声音低哑。
“不是我要,是天要!”姑姑猛地站起,眼中燃着烈火,“你以为报了一个林正南就够了?真正该死的,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共犯!是你父亲呕心沥血编撰《文脉志》时,背后捅刀的同僚;是你母亲被掳后,装聋作哑的族亲!他们才是让正义永不能昭雪的根源!”
戒色沉默良久,终是摇头:“若再杀下去,我与林正南何异?以暴制暴,终成魔道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!”姑姑怒喝,“难道让他们继续高坐庙堂,享尽荣华,而你父母的冤屈,只能随江水东流?你母亲的耻辱,就此湮灭无闻?”
屋外thunder隆隆,一道闪电劈下,照亮两人对峙的身影。
戒色缓缓闭眼,再睁开时,眸中已无挣扎,唯有决断。
“不杀人,但揭罪。”他说,“你手中有‘换籍录’,我有佛门人脉、民间声望。我们不必动手,只需将真相公之于众。让百姓知其伪,让朝廷查其罪,让天下还一个公道。”
姑姑怔住:“你想走正途?可这世道,黑白颠倒,哪有公正可言?”
“正因为没有,才更要有人去做。”戒色起身,望向窗外风雨,“我是僧人出身,虽已离寺,却仍信因果。杀人得果报,揭恶亦得果报。但我宁可背负骂名,也不愿再沾无辜之血。”
姑姑盯着他看了许久,忽然笑了,笑声凄厉如夜枭:“好啊……林家血脉未断,倒是多了几分迂腐书生气。罢了,随你。但我警告你??若有人阻你揭真相,别怪我不讲情面。”
她转身欲走。
“姑姑。”戒色叫住她,“保重。”
她脚步微顿,未回头,只留下一句:“等你母亲百年之后,再来找我。那时,该算的账,一笔都不会少。”
雨停时,东方既白。
接下来的日子,戒色开始秘密联络旧识。他写信给昔日寺中师兄弟,请他们代为传抄“换籍录”内容;又通过采药人、商旅,将碎片信息散播至邻县。他不敢署名,只以“文渊遗孤”自称,附一首诗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