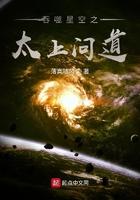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安史之乱:我手握十万兵马 > 第117章 鱼符为信暗线连蜀(第1页)
第117章 鱼符为信暗线连蜀(第1页)
夜色如墨,泼洒在恒州城的每一寸砖瓦上。
子时的更鼓声刚刚敲过,沉闷而悠远,像是在为这座乱世中的孤城敲响丧钟。
北门下方的暗道,潮湿的土腥气与铁锈味混杂在一起,火把的光影在狭窄的甬道壁上疯狂舞动,将人的影子拉扯得如同鬼魅。
薛七郎在前引路,他那身标志性的青衣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,只有腰间刀鞘上的银饰偶尔闪过一丝寒光。
他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衣人,步履踉跄,每一步都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
浓重的血腥味从那人身上散发出来,即便是在这污浊的空气中,也显得格外刺鼻。
影驿的密室里,灯火通明。
与外界的阴冷截然不同,这里温暖而干燥,西壁的书架上排满了卷宗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药草的味道。
黑衣人被扶到一张榻上,他艰难地抬起手,摘下了头上的斗笠。
火光映照下,一张年轻却写满疲惫与坚毅的脸庞显露出来。
他的嘴唇干裂,脸色苍白如纸,但那双眼睛,却像是在绝境中燃烧的火焰,充满了不屈。
“陈元礼之子,陈奉先,见过赵使君。”他的声音沙哑,却字字清晰。
赵襦阳的目光落在他左臂上缠绕的血布上,那里的鲜血己经浸透了厚厚的布条,凝成了暗红色的硬块。
他没有立刻说话,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。
陈奉先仿佛没有察觉到自己的伤势,用唯一能动的右手从怀中摸索着,取出一件东西,郑重地放在身前的案几上。
那是一块铸造精良的铜鱼符,只有半枚,断口处崭新而锐利。
鱼身上的鳞纹繁复而古老,在烛光下闪烁着幽暗的光泽。
赵襦阳的瞳孔微微一缩。
他伸出手,从袖中取出另一件物事——正是李泌悄然留下的那半枚铜鱼符。
两块残符轻轻合拢,伴随着一声微不可闻的“咔哒”声,一条完整的铜鱼严丝合缝地呈现在众人眼前,仿佛从未被分开过。
密室内的空气瞬间凝固。
“家父有令。”陈奉先深吸一口气,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沉声说道:“杨氏乱政,秽乱宫闱,贵妃当诛。此为清君侧,为社稷除害。然,天子西狩入蜀,并非社稷之福。如今太子北上,欲在灵武自行登基,恐开天下藩镇效尤之祸。河北,乃天下忠义之所在,若河北不发声,天下将再无正声!”
他的话语如同一记重锤,敲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。
马嵬坡兵变,这件震惊天下的大事,其核心人物的儿子,此刻就带着血与火的气息,将最隐秘的内情和最沉重的请托,送到了恒州。
赵襦阳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枚完整的鱼符,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,让他纷乱的思绪瞬间变得清晰。
他没有回应陈奉先的话,而是侧头对侍立一旁的戚薇吩咐道:“戚先生,为陈公子疗伤。”
戚薇躬身领命,立刻上前,小心翼翼地解开陈奉先臂上的血布。
当伤口暴露在空气中时,连见惯了生死的薛七郎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
那是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,皮肉翻卷,显然是在突围时留下的。
在戚薇为陈奉先处理伤口时,赵襦阳看似随意地问道:“陈将军既己掌控禁军,为何不护送陛下安然入蜀,反而任由太子殿下北上灵武?此举,恐非人臣之道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,却像一根针,精准地刺向了问题的核心。
陈奉先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,牵动了嘴角的伤口,他嘶了一声,才缓缓道:“使君有所不知。禁军将士,皆是关中子弟,父母妻儿俱在京畿。他们诛杀杨氏,是出于义愤,却不愿背井离乡,远赴蜀道。家父……家父曾言:‘我等此举,是为清君侧,而非夺君位。’然则,箭己在弦,势己铸成,再难回头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目光灼灼地看向赵襦阳,眼神中带着一丝恳求:“家父托我将此符信交给使君,并非为了陈家私情,实为大唐江山留下一线正统!若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,望使君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,不要兴兵拒绝;可若是他倒行逆施,有负社稷,亦望恒州能……能为天下,制之!”
话音未落,陈奉先猛地挣脱戚薇的搀扶,翻身下榻,朝着赵襦阳的方向,重重地叩首在地。
额头与青石板的碰撞声,在寂静的密室中回响,无比清晰。
这一拜,拜的不是赵襦阳个人,而是拜托他肩负起制衡新君、匡扶社稷的千钧重担。
薛七郎立刻上前将他扶起,他连夜取来影驿秘藏的《阴符经》卷宗,仔细比对鱼符背面的印契,又核对了其中暗藏的“左龙武军”调兵密语,最终向赵襦阳点头确认:“主公,符是真的,印契无误。”
一旁的陈砚舟却眉头紧锁,忧心忡忡地低声道:“主公,此事蹊跷。万一这是杨氏余党,或是朝中其他势力设下的局,故意引诱我们与未来的新君为敌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