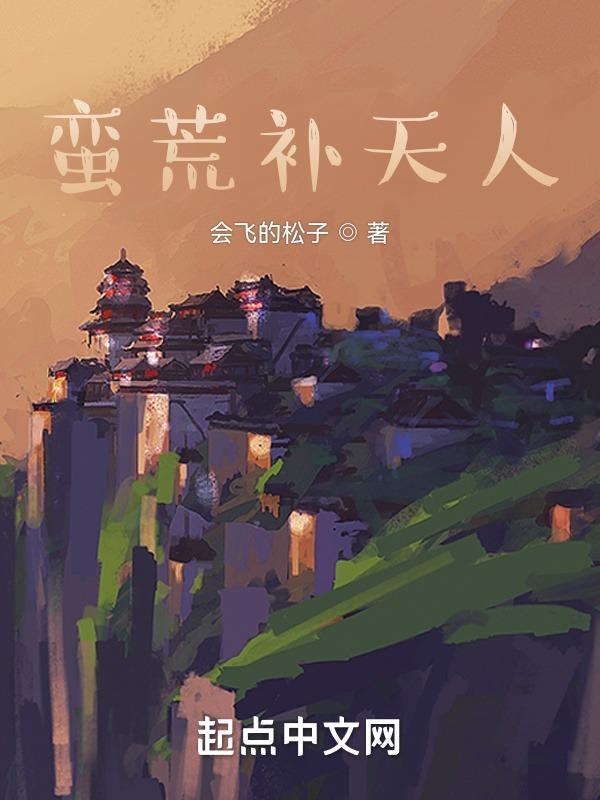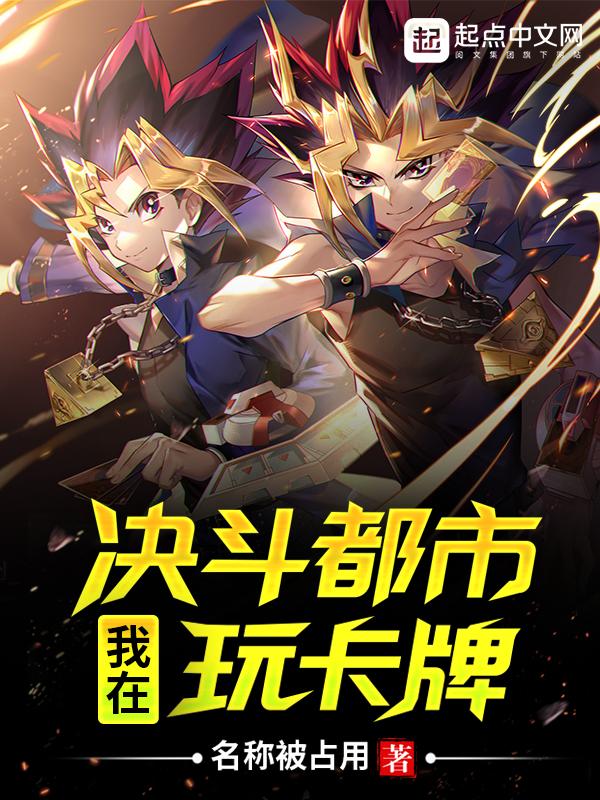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我讲烛影斧声,赵光义你哭什么? > 第174章 咱大明怎么迁都去北平了(第1页)
第174章 咱大明怎么迁都去北平了(第1页)
武英殿内,朱元璋胸膛为之剧烈起伏。
眼睛都有些红了!
双手死死的按在桌案上,似乎那手指要将桌案都给穿透一样。
只觉得胸膛都要爆炸了!
愤怒!
极其的愤怒!
虽然不少。。。
“林清远不是第一个,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”
笔尖微微一顿,墨迹在纸上洇开一小团,像一滴未落的泪。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,落在桌角那枚滇缅公路的铜纽扣上,泛出青铜色的光晕。它静默地躺在那里,仿佛一个不肯闭眼的见证者。
我忽然想起沈璃发来的另一条消息:“格尔木疗养院第三层的地基扫描有异常震动,频率与‘心灯云’激活时的波段完全一致。我们不确定这是自然现象,还是……某种回应。”
某种回应。
这个词让我脊背发凉。祖父的影像、林清远的倒计时、那些藏在五线谱和谜语里的真相??它们不是终点,而是一场更大共振的序曲。就像地下暗河终于冲破岩层,声音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第二天清晨,我带着录音设备去了城郊的老殡仪馆。那里曾是“清源计划”外围档案销毁点之一,如今已废弃多年,墙皮剥落,铁门锈蚀。但据一位退休工人说,每逢雷雨夜,地下室还会传出打字机的声音。
他叫老周,七十八岁,当年负责焚烧文件前的分类登记。他坐在轮椅上,手抖得厉害,说话断断续续:“不是鬼……是机器。一台老式电传打字机,编号D-7。那天晚上,它自己启动了。纸带哗啦啦往外吐,全是没人认识的符号。我们以为坏了,想拔电源,可它……它写了三个字??‘我在’。”
他说完,猛地抓住我的手腕,眼睛睁得极大:“你爷爷的名字,出现在最后一行。”
我随他进入地下室。积水没过脚踝,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焦纸的气息。角落里,那台打字机果然还在,外壳漆黑,按键泛黄,像是从未被移动过。我蹲下身,轻轻拂去灰尘,在机身底部发现一行小字:**制造于1964年,北京自动化研究所,项目代号:回声**。
“回声?”我低声念出。
老周一愣:“这上面没写这个啊。”
我的心跳骤然加快。这行字,是后来刻上去的,刀痕很新。
当晚,我把打字机运回仓库,请王小川联系中科院的老专家做检测。结果令人震惊:这台机器内部没有存储芯片,却有一种类似生物神经网络的金属纤维结构,能对外界电磁波动产生反应。更诡异的是,当我们将“心灯云”的初始代码音频播放给它听时,打字机自动启动,纸带缓缓吐出:
>**“记忆具有质量。当足够多人同时回忆同一事件,现实会发生微小偏移。”**
>**“这不是幻觉,是量子历史态的坍缩。”**
>**“林清远发现了这一点。所以他选择死,让自己的死亡成为锚点。”**
纸带戛然而止。
王小川脸色发白:“你是说……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,不只是在揭露过去?而是在……改写它?”
我沉默良久,抬头看向墙上那幅地图??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全国各地的“记忆节点”:云南的滇缅公路纪念碑、东北的劳改农场旧址、西北的核试验基地周边村庄、南方某海岛上的战地医院遗址……每一个点,都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坚持“我记得”的地方。
“也许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。”我说,“而是一个不断折叠的平面。我们以为过去了的事,其实只是沉睡在褶皱里。只要有人唤醒,它就能重新浮现。”
就在这时,手机响了。是青海那边的技术员,声音颤抖:“昭老师,格尔木的第二密室……变了。”
“什么变了?”
“那台放映机不见了。原地只留下一卷新的胶片,标签上写着:‘给未来的你。’我们不敢放,但它……在发热,像是刚运行过。”
我立刻订了最近的航班。
高原的风依旧凛冽,可当我再次踏入地下密室时,空气中竟有一丝暖意。那卷胶片静静躺在石台上,表面覆盖着细密的水珠,仿佛刚从某个活体中取出。技术人员告诉我,红外扫描显示胶片内部嵌入了微型晶体阵列,储存容量远超现代技术。
“我们尝试用祖父那台放映机播放,失败了。但……它似乎只认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