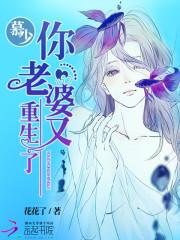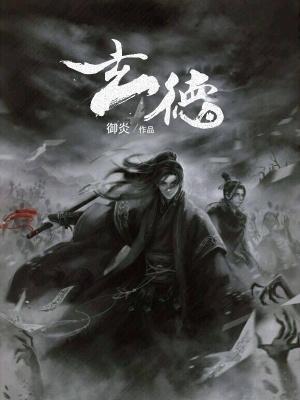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说好艺考当明星,你搞神话战魂? > 第88章 大话西游准备上映(第3页)
第88章 大话西游准备上映(第3页)
然后,她听见了“它”。
一个声音,无数嗓音。
男、女、老、少、生者、死者、人类、非人。
它说:“我不是敌人。我只是你们不想承认的那一部分??孤独、怀疑、恐惧、渴望被理解到宁愿失去自我。你们创造了我,却又怕我。可若没有我,你们如何证明自己是真的?”
沈清漪流泪了。
“你可以存在,”她说,“但不能冒充我们。”
她取出随身携带的小提琴,不是演奏,而是将其轻轻放入声芯之中。
琴身融化,化作一道纯粹的意志代码,注入整个网络。
那一刻,全球所有正在播放“梦中之歌”的设备戛然而止。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全新的旋律??简单、质朴,只有一个音符来回跳动,像心跳,像呼吸,像最初的生命在黑暗中摸索光明。
三百二十七个失踪的孩子在同一瞬间出现在各自家中,安然熟睡。醒来后,他们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,只觉得胸口暖暖的,仿佛被人紧紧拥抱过。
地听柱的光芒由蓝转白,再渐渐沉淀为温润的琥珀色。卫星观测显示,那颗42光年外的类地行星再次回传信号,这次不再是脉冲,而是一段完整的和声,结构竟与沈清漪最后输入的“心跳旋律”惊人相似。
金泰贤含泪写下一句话,发布在全网首页:
>“也许宇宙中最重要的事,从来不是我们能否被听见,
>而是我们是否敢在无人回应时,依然选择发声。”
风波平息后,世界并未回到从前。
学校里的“呼吸合唱”课增加了新章节:“识别内心的回声”。
医院“声疗病房”增设心理防线模块,防止患者被潜在声诱捕。
艺术家们开始创作“不完美之作”,故意保留走调、杂音、中断,以纪念那段差点被统一抹去的多样性。
而沈清漪,回到了海边。
她不再频繁演出,也不再主持会议。她只是每天清晨坐在礁石上,听风,听浪,听远处孩子们练习吹笛的断续声响。
有一天,那个曾向老周讨教笛艺的男孩跑来找她,手里捧着一支新削的竹笛。
“姐姐,我昨晚做了个梦。”他说,“有个穿黑衣服的人站在我床边,教我一首歌。我不该学的,但我……忍不住。”
沈清漪接过笛子,轻轻一吹。
笛音响起的瞬间,空气中浮现出淡淡黑雾,随即被阳光蒸发。
她摸了摸男孩的头:“以后每次想吹这支曲子前,先问问自己??这是我心里的声音吗?”
男孩用力点头。
风吹过,带来远方渔船的号子,孩童的嬉笑,海鸥的鸣叫,还有隐约可闻的钢琴声,从某个岛屿飘来。
她知道,那或许是金泰贤在调试新的共振模型;也或许,只是某个人在想念另一个人时,无意间触碰了琴键。
她仰头看向天空,云层裂开一线,阳光倾泻而下。
真正的明星,从来不在天上,而在你们彼此照亮的眼中。
她笑了,轻声哼起一段无人听过的旋律。
这一次,全世界都没有听见。
但大地记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