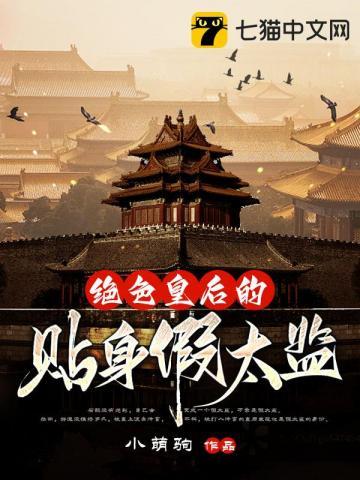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红楼芳华,权倾天下 > 第167章 李桂姐的救赎2(第2页)
第167章 李桂姐的救赎2(第2页)
她挪动着灌了铅似的双腿,一步一挨走到西门庆面前,双膝一软,噗通一声跪倒在地,声音哽咽却清淅:“奴婢…桂姐儿…见过大爹…”
西门庆哈哈一笑,望着这李桂姐。
只见粉黛尽洗,铅华不施,一张瓜子脸儿素净得如同初雪新剥的嫩菱角,只馀下那天然一段风流态度。
两道笼烟眉细细弯弯,此刻因着哭泣,微微蹙着,恰似西子捧心,更添了十二分的可怜。这娇弱媚态真真是:梨花带雨,海棠含露,别有一番揉碎人心的风流。
大手一伸,稳稳将她搀扶起来,顺势便握住了那冰凉颤斗的小手,温言道:“傻姐儿,哭什么?我可没有那八抬大轿、凤冠霞帔的排场来接你。只有门外一匹马,倒也筋骨强健,驮得动俩人。便如那晚一般,你可…愿意?”
李桂姐哪里还说得出话?只觉一股热流从被握住的手心直冲头顶,满心满肺都被这从未有过的踏实填满了。
她仰起泪痕斑驳的脸,望着西门庆那带着三分怜惜七分笃定的眼睛,只顾得拼命点头。那泪珠儿,便随着她点头的动作,大颗大颗地洒落在尘埃里。
却说外面月色昏黄,疏星几点。
西门庆那匹健马驮着二人,踢踢踏踏行在寂聊的街巷上。
李桂姐缩在大官人宽阔滚烫的怀里,身子犹自簌簌轻颤。方才丽春院里那场雷霆风暴、地狱轮回,此刻竟真真儿换做了这暖玉温香的怀抱。
她只觉得云里雾里,魂灵儿尚未归窍,脑子里一片混沌空白,只晓得使出吃奶的力气,死死贴住大官人那坚实如铁的胸膛,恨不能把自己揉碎了嵌进去,唯恐这不过是黄粱一梦。
西门庆一手控缰,一手却稳稳圈着她纤细的腰肢,低头嗅着她身上的味儿,半晌,方慢悠悠开了口,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淅,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:
“桂姐儿,如今你既是我西门府上的人了,有些丑话,免得日后心里存了疙瘩,爷不得不说在头里。你竖起耳朵,好生听着。”
李桂姐在他怀中忙不迭点头,如同捣蒜,闷闷应道:“奴婢…听着呢…大爹…”
西门庆箍在她小腹上的那只大手,温热厚实,恰好替她严严实实挡住了深秋夜风直侵肚腹的寒凉。
李桂姐感受着这份霸道里透出的体贴,心尖儿又是一颤,连带着说话的声音也愈发柔腻似水:“大爹…只管吩咐…”
“方才…”西门庆顿了顿,气息拂过她耳廓,“…怨不怨爷最后还摆你一道,试你一试?”
李桂姐想也未想,脱口而出:“奴婢不怨!”
嗬…”大官人喉间发出一声低沉的轻笑,那笑声在厚实的胸膛里嗡嗡震动,震得李桂姐心尖儿也跟着一颤一颤,酥酥麻麻的。
“真不怨?小油嘴儿…”他低下头,温热的气息有意无意地拂过她敏感的耳垂,“…单凭你这张小嘴儿,哄得爷骨头缝里都发酥倒是容易。只是…”
他故意顿了顿,圈在她腰腹的手臂紧了紧:“…若是今这甜丝丝的话里,掺了半星儿虚言,将来被爷摸清了底细…”
“爷那西门府上的‘家法’…可不似你们丽春院的鞭子差!”
李桂姐越发地往那滚烫的怀里揉,摇了摇头:“真不怨!奴婢说的是真话。”
她仰起那张在月色下愈发显得楚楚可怜的小脸,眼波流转,似嗔似怨:“要怨…也只怨奴婢命里没托生个好人家,白担了这官妓的贱名儿…由不得自己个儿清清白白、大大方方地…配您…”
她仰起粉颈,泪光点点,痴望着西门庆月色下棱角愈显深邃的下颌。
积了十数载的酸楚并着痴念,如决了堤的洪水,冲口而出:“大爹爹…您…您可知奴婢平日里,心窝子里翻腾得最勤的是什么?”
大官人箍在她小腹的手略松了松力道,鼻子里只“唔?”了一声,算是应了。
李桂姐觉着那指腹上的温热与力道透衣传来,心尖儿上那点子念想破土钻出,声音柔媚得能掐出水,却浸透了无边的凄惶:
“奴婢…奴婢总痴想着…徜若…徜若奴托生在个正经的官宦门庭,或是富贵乡里的千金小姐…清清白白的身子,干干净净的名声…这般遇上大爹爹您!”
“不是在丽春院那等乌烟瘴气、处处算计的腌臜地界…而是…或是在梵音袅袅的佛寺里拈香,或是在草长莺飞的郊野踏青,又或是火树银花的元宵灯市…”
“你我就隔着那熙攘人潮,不经意地…那么一对眼儿…”她痴痴诉着,眼神迷离,恍如真见了那镜花水月的幻境,“许是…许是便如那戏文里唱的…公子遇佳人”
“可惜…”她声气低下去,唇边绽开一个苦极的笑涡,“奴不过是个官妓,那等不堪之事便是奴的本分…便是遇着大爹爹您时,也才刚卖了自家姑母…大爹爹不信奴,也是该当的。”
大官人嘴角噙笑,道:“那我再问你,你也要用真话回我。是什么根由,教你心念这般牢靠?只管说我绝不生气,图财帛也好,图跟着我图个安稳也罢。”
“大爹爹说的都在理,却也…不全在理。”李桂姐轻声道。
“哦?”这倒有些出乎意料。
“若说不图财帛安稳,那是哄人的鬼话。奴打落地起,最大的念想便是爬出那口腌臜泥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