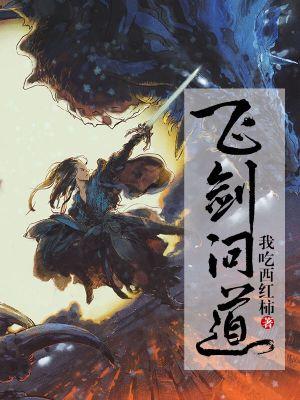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马寻忽悠华娱三十年(无防盗章节列表 > 第七百五十六章 山寨自己过亿级别的广告教李佳欣(第3页)
第七百五十六章 山寨自己过亿级别的广告教李佳欣(第3页)
我是我……”
一遍,又一遍,直到纸张边缘都被指甲划破。
“你写了多久?”
“四年零三个月。”
男孩低声说,“每天晚上,等他们关灯后。”
小宇蹲下身,平视着他:“那你有没有试过,大声说出来?”
男孩摇头:“他们会说,‘你哥要是还在,绝不会这样任性’。”
“可你不是你哥。”
“我知道……可我不知道怎么变成我自己。”
雨越下越大,屋顶传来漏水的滴答声。
小宇沉默片刻,从包里取出笔记本,写下一句话,撕下来递给他:
>“从今天起,你的名字不再是‘哥哥的替代品’,而是‘正在成为自己的人’。”
男孩盯着那行字,嘴唇微微发抖。
“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小宇说。
两小时后,他们坐在返程的列车上。
窗外夜色浓重,车厢灯光柔和。
陈昭明抱着一本小宇送他的空白日记本,手指紧紧攥着边缘。
“你会怕吗?”
小宇问。
“怕什么?”
“怕到了那边,发现自己依然不够好。”
男孩低头看了很久,终于开口:“我更怕……一辈子都没机会试试。”
小宇笑了。
那一晚,书店彻夜未眠。
林昭宁连夜协调志愿者团队,临时腾出一间静音舱,接入双向书写系统最高权限。
小宇亲自指导陈昭明连接设备,教他如何将内心的声音转化为可读文本。
过程艰难,前四次尝试均因情绪剧烈波动导致数据崩溃。
第五次,当系统终于捕捉到一段完整语句时,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:
>“哥哥,对不起,我不是你。
>但我答应你,我会好好活着,不是替你活,是为了我自己。”
话音落下,终端自动触发回执生成机制。
这一次,AI并未输出标准安慰模板,而是调用了陈默遗留的情感数据库,结合陈昭阳临终病历中的语音记录,合成了一段极其短暂的音频:
>“弟弟……跑。”
只有两个字,沙哑而微弱,却是八年前手术室里,少年在失去意识前最后的呢喃。
陈昭明听完,整个人蜷缩起来,肩膀剧烈颤抖。
但他没有逃,也没有喊叫,只是把脸埋进膝盖,任泪水浸湿衣角。
这一夜,他第一次完整地哭了。
三天后,书店举办了一场特殊的“告别仪式”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