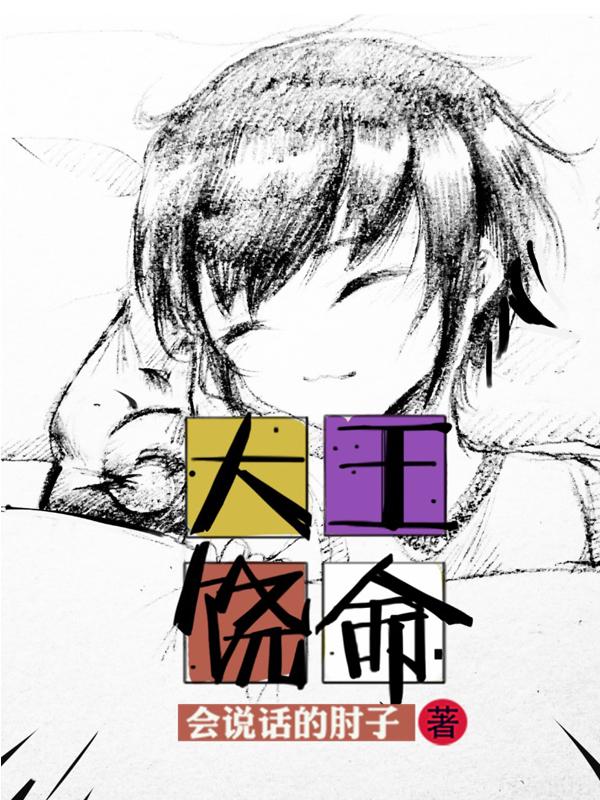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方言朱琳重生1977大时代小说TXT全集免费阅读 > 第1473章 周兆琴的大礼(第2页)
第1473章 周兆琴的大礼(第2页)
垄断权的放弃,以及,在万人高呼你名字时,仍能转身走入人群,变成一个普通提问者的勇气。
夜更深了。
湖面传来细微的裂响,冰层正在缓慢融化。
春天终究来了,哪怕带着犹豫和反复。
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,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轻响。
来人走得不快,却坚定。
“是你吗?”
声音苍老,带着西北口音。
我点头,随即意识到对方可能看不见。
“是我。”
老人在我身旁坐下,裹紧军绿色棉袄。
他身上有股陈年烟草味,混合着药膏的气息。
“我是第十三号哨所最后一任站长。”
他说,“1982年调来的,待了六年。
后来上面说项目终止,让我们撤离。
没人解释为什么。”
我静静听着。
“你们的事……我听说了一些。”
他低声道,“昆仑山那天晚上,整个青藏高原的无线电都中断了十分钟。
气象卫星拍到一道银色光柱从地面冲向平流层,持续了三十七秒。
官方说是极光异常,可我知道不是。”
我依旧沉默。
“我在那里守了那么多年,每天记录气温、风速、云层变化,可从没想过,那台终端真正测量的,从来不是天气。”
他苦笑一声,“而是人心的波动阈值。”
我心头微震。
“你也感觉到了吧?”
他转头看我,尽管我知道他未必看清我的脸,“最近几个月,全球‘异常心理报告’数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二。
抑郁症发病率小幅回升,但自杀率骤降。
最奇怪的是,各国监狱里的囚犯开始主动写忏悔书,不是为了减刑,而是……因为他们终于敢面对自己了。”
我缓缓点头。
这就是“烛火协议”
最后的回响。
当一个问题被听见,它就不再吞噬提问者。
人们不必再伪装坚强,也不必把痛苦当成勋章佩戴。
他们只是说:“我害怕。”
“我觉得对不起谁。”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而这,正是自由的起点。
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铁盒,递给我。
“这是我在清理旧档案室时找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