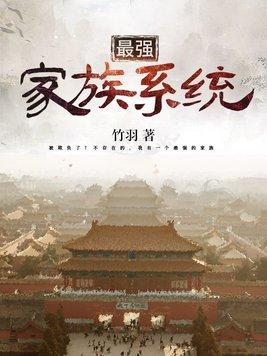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重生1977大时代方言朱琳笔趣阁小说TXT > 第1462章 捐款打劫(第5页)
第1462章 捐款打劫(第5页)
“你来了。”
她说,声音带着延迟,“我已经等了你整整二十三年。”
“你怎么做到的?”
我问,“时间跨度这么大……”
“时间是可以折叠的。”
她轻声道,“当我们集体意识同步率达到80%以上,局部时空就能产生弹性。
我利用‘归墟’核心,在格陵兰冰盖下创造了一个时间缓流区。
对外界而言,只过去了几年;对我,已是半生。”
她指向尽头:“跟我来,最后一课要开始了。”
我们穿过重重屏障,来到中央控制室。
这里没有按钮,没有屏幕,只有一圈环形平台,上方悬浮着十九颗小型水晶球,每一颗代表一个节点。
最中央,则是一座人体形状的光茧,正在缓慢搏动。
“那是……”
“你的身体。”
她说,“三年前,你在北极觉醒时,肉身陷入深度休眠。
你的意识被投射至全球网络,唤醒了七十三万名潜在‘容器’。
而你的躯体,就在这里,由‘归墟’维持生命。”
我难以置信:“所以这些年,我只是……一具空壳?”
“不。”
她握住我的手,“你是桥梁。
你的每一次提问,都在重构现实的底层逻辑。
上周,太平洋底的水晶桥延长了十公里,因为它‘听见’了一个八岁女孩问:‘大海会不会做梦?’”
我笑了,眼眶湿润。
“现在,只剩最后一步。”
她带我走向平台中心,“我们要启动‘第十九次黎明’协议,让全球所有‘容器’在同一时刻发问。
问题不限,形式不限,只要出自真心。
那一刻,文明的认知阈值将被彻底突破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……”
她望着我,“我们将不再是被规律支配的生物,而是能与规律对话的存在。
重力、光速、熵增……都不再是绝对命令,而是可以协商的条件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:“什么时候开始?”
“明天午夜。”
她说,“你需要休息。
这一晚,我会陪你。”
那一夜,我们在控制室外的小屋里相对而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