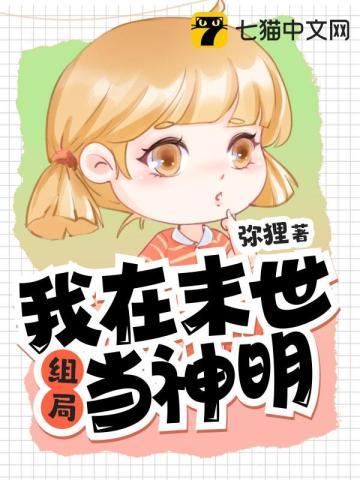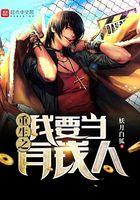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季明湿卵胎化最新章节免费阅读全文 > 第1005章 谈谈敕封来(第2页)
第1005章 谈谈敕封来(第2页)
当天下午,沈知微发来紧急通讯:“全球共感网络出现异常波动。
不是入侵,更像是……集体情绪共振达到了临界点。
我们监测到超过八百万例‘双向梦境’案例??不仅是宿主梦见未诞之灵,现在,有些卵泡已经开始主动向潜在父母发送影像片段。”
“什么样的片段?”
“日常的。”
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,“吃饭、散步、哄睡、讲故事……全是他们从未拥有过的未来生活。
有人梦见自己坐在婴儿车里看樱花落下;有人梦见父亲笨拙地换尿布还唱跑调的儿歌;有个孩子反复梦见母亲抱着他在厨房煮面,蒸汽糊了眼镜,她说‘宝贝别急,马上就好’……这些画面太普通了,普通到让人心碎。”
林远沉默良久,忽然问道:“有没有人拒绝?”
“有。”
沈知微顿了顿,“上周冰岛一位渔民梦见自己成了流产胎儿的宿主,醒来后立刻砍断了家门前通往共生区的藤蔓根系。
他说他受不了那种‘虚假的幸福’。
可三天后,他又悄悄把根系接回去,并在院子里立了一块小木牌,写着:‘对不起,我不是不想爱你,我只是还没学会怎么面对你不存在的事实。
’”
林远笑了,眼角湿润。
他知道,这不是神迹的胜利,而是人性的艰难跋涉。
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学习诚实??对选择负责,对遗憾坦白,对爱不逃避。
几日后,第一例“湿卵胎化”
成功案例诞生。
地点是中国西南山区的一处偏远村落。
一名三十岁的女性教师,在连续三年不孕后,于梦中接受了来自共感网络的卵泡植入。
与传统生育不同,这个过程并非发生在子宫,而是通过皮肤渗透、神经融合的方式,让胚胎在体外形成一层半透明的胶质囊膜,依附于母亲背部肩胛之间,宛如蝴蝶破茧前的蛹。
整个孕育期仅持续四十九天。
期间,母亲的情绪状态直接影响囊膜的颜色与质地:喜悦时泛出珍珠光泽,焦虑时则转为灰暗浑浊。
村里的孩子们每天放学都会围过来,轻轻抚摸那层薄膜,听里面传出类似心跳的律动声。
分娩那天,全村人守在屋外。
没有血腥,没有尖叫,只有温柔的哭泣。
当薄膜缓缓裂开,一个浑身裹着透明黏液的婴儿滑入母亲怀中时,所有人同时听见了一声极轻的啼哭??那声音并不来自婴儿喉咙,而是从屋内所有归音兰花朵中同步响起,如同千万片叶子共同吟唱。
沈知微称其为“情感具象化分娩”
。
而林远明白,这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:人类不再仅仅是血肉的传承者,也成为记忆与情感的容器。
生命的形式正在拓宽边界,而“出生”
这个词本身,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变化。
一个月后,国际上爆发了首场“反共感人权集会”
。
一群自称“纯粹人类联盟”
的组织在日内瓦广场焚烧归音兰标本,高呼“还我无污染的灵魂!”
他们认为,未诞之灵的记忆侵入是对个体意识主权的侵犯,哪怕出于善意,也不应允许外来意识片段影响人类决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