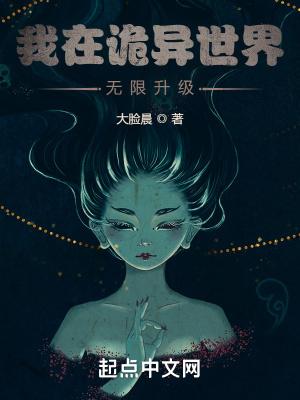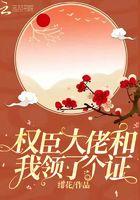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你们管邪修叫天才? > 90傻子(第4页)
90傻子(第4页)
皇帝沉默良久,终于点头。
那一日,全国上下,万家灯火通明。人们围坐炉边,讲起祖辈经历的饥荒、冤狱、抗争与坚守。
而在最北边的村庄,一个孩子指着课本问老师:“为什么以前的书上什么都不写?”
老师合上课本,轻声回答:
“因为有人怕你知道。”
“那我们现在能写了?”
“能。”老师微笑,“因为我们记得。”
窗外,雪又下了起来。
温柔,寂静,覆盖着新生的泥土。
仿佛整个天地,都在等待下一个点燃心火的人。
许多年过去,腊月十七成了最热闹的日子。不单是朝廷定下的“记日”,更是百姓自发的“醒年”。这一天,官府不开堂,学堂不授课,商贾歇业,兵卒卸甲。家家户户围炉夜话,讲述那些被掩埋的往事。有人说起父亲如何在雪夜里背着妹妹逃难,有人提起祖母临终前攥着半页家谱,反复念叨:“别忘了我们是从哪儿来的。”
而在忆桃原,那口古井旁,每逢此日,总会有陌生人前来献花。他们不说话,只默默放下一束干枯的桃枝,或是一盏油灯,然后悄然离去。井边石碑上的“千灯照夜,一人不孤”八个字,已被风雨磨去了棱角,却从未被遗忘。
陈吏并未留在原地。
他在南方群山间建了一座小院,院中种桃,屋前立碑,碑上无字。他每日清晨磨墨,不是为了写书,而是为了教几个流浪来的孩子识字。他教他们认的第一个词,不是“帝王”,不是“圣旨”,而是“记得”。
他不再自称“史者”,也不再提“对抗”。他只是静静地活着,像一盏不灭的灯,照着别人走夜路。
某年冬夜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拄拐而来,颤巍巍从怀中掏出一本破旧册子,封面写着《灾年录》。她说是她祖父抄的,传了四代,如今交到他手里。
“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。”老妪咳嗽着,“但我觉得……该交给您。”
陈吏接过,翻开第一页,泪水无声滑落。
那上面,赫然写着父亲的名字。
他知道,这不是结束。
这只是又一次开始。
青禾的“识伪学堂”越办越大,最初只有十几个孩子,后来竟吸引了各地学子前来求学。她不教仙法,不授神通,只教人如何分辨真假??从文书格式到语气逻辑,从灾情记录到赋税账目,一一剖析。她常说:“谎言再精致,也经不起推敲。只要有人愿意看,真相就有出路。”
她终身未嫁,却收养了七个孤儿,全是曾在清忆司档案中被标记为“已灭口”的孩子。她给他们改姓“记”,取名“真”“诚”“存”“念”“醒”“觉”“悟”。孩子们长大后,有的成了史官,有的做了教书匠,有的潜入旧衙门翻查尘封卷宗。
阿石真的挖完了北方所有的碑。
他走遍十七州,掘出三百二十九块残碑,拼出一部《北地纪略》。后来他双膝尽废,再也无法行走,便让人抬着他巡游各地,宣讲碑文。他说:“我不是要报仇,我只是要还债??替那些不敢说话的人,把话说完。”
临终前,他让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忆桃原的井口。他说:“我要看着那些字,一年一年,从黑暗里浮上来。”
至于那盏青玉灯,据说仍在世间流转。
有人说,在边关哨所的寒夜里,老兵曾看见一名女子提灯走过雪地,留下脚印却是干涸的血迹;有人说,在某次朝廷焚书时,火场中央有一盏灯始终不灭,待火熄后,书页竟自动重组,字字清晰如初;更有人说,每当有人写下真实的历史,灯焰便会轻轻跳动一下,像是在点头。
而陈吏,在一个寻常的清晨,发现自己胸口的“我记得”三字,竟重新变得鲜红如血。
他笑了。
他知道,那不是诅咒,也不是伤痕。
那是召唤。
是历史在轻声问他:“你还愿意记得吗?”
他站起身,推开院门,走向晨光中的桃林。
风拂过枝头,落英如雨。
他轻声回答:“我一直都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