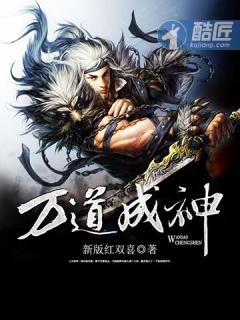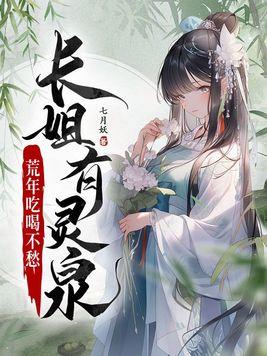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恋爱疗愈手册 > 第141章 神来一笔(第1页)
第141章 神来一笔(第1页)
商讨过后,消防队长决定让急救医生冒险将伤者相叠处的空间再延伸一些,这样有了空间,就可以用两把钳子伸进去,一个用来稳定住下患者身体内金属构件的位置,另一个用来实施切割。
在此过程中,辛苦的除了两位。。。
雪在深夜停了,凌晨三点十七分,林小满醒来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何睁开眼,只是忽然觉得空气中有种微妙的震颤,像一根极细的弦被轻轻拨动。窗外,月光穿过云层缝隙洒在庭院里,积雪泛着冷蓝的光泽,仿佛整座静屿正沉入一场缓慢而深沉的呼吸。
她披衣起身,赤脚踩过木地板,走到厨房烧水泡茶。水壶刚响,门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??是李澜。她穿着厚实的羊毛外套,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,发梢沾着未化的霜粒。
“你也睡不着?”林小满问,声音很轻,怕惊扰了夜的寂静。
李澜点头,在桌边坐下,将纸袋推到中间。林小满打开,里面是一叠炭笔画稿,每一张都画着同一个人:程远。有的是他低头走路的背影,有的是他坐在湖边抽烟的侧脸,还有一张,是他站在低语室门前犹豫的模样,手指悬在门把上,眼神像是即将坠入深渊又被人拉住。
林小满怔住。“这些……你什么时候开始画他的?”
李澜低头写下:“从他来的第一天。我一直在观察他怎么活着??不是作为‘幸存者’,而是作为一个还会颤抖、会退缩、会害怕的人。”她顿了顿,继续写,“我想记住这种真实。因为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。”
林小满看着那些线条,每一笔都带着克制的温柔。她忽然明白,李澜并不是在画程远,而是在借他的存在,练习如何接纳自己的脆弱。
“你想让他看到吗?”她问。
李澜沉默良久,最终摇头,然后补了一句:“但现在还不行。我要先学会,不靠别人的回应来确认自己值得被看见。”
林小满笑了,倒了一杯热茶递给她。“你知道吗?这大概是你说得最长的一句话了。”
李澜也微微弯起嘴角,那笑容淡得几乎看不见,却像破冰的第一缕阳光。
天亮前,她们一起把画收进档案柜,贴上新标签:“李澜?冬?人”。出门时,晨雾弥漫,远处传来陈默修理温室屋顶的声音,锤子敲打金属的节奏稳定有力,像是某种无声的承诺。
早餐后,小舟带来一封来自青海的信。寄信人是一位牧民的妻子,丈夫因雪崩去世三年,她一直无法走出帐篷,直到读到静屿官网上转载的一段音频??正是那位退伍军人留下的三分钟沉默录音。
她在信中写道:
>“原来不用说话也可以被听见。
>我第一次敢对着风说‘我想他’。
>那天晚上,我梦见他牵着马回来,脸上有笑。
>我知道那是假的,但我的心,好像真的松了一下。”
随信附着一小块手工压制的牦牛奶酪,包装纸上用藏文写着“谢谢”。
林小满读完,眼眶发热。她让小舟把信复印十份,贴在公共休息区的墙上,并在下方加了一行字:“沉默也是语言的一种形式,请尊重每一个不愿开口的灵魂。”
当天下午,程远主动提出要教孩子们画画。他说不出具体想教什么,只说想试试“让人画出他们说不出的东西”。美术教室临时改造成工作坊,几张长桌拼在一起,铺满白纸和彩色铅笔。十几个孩子陆续进来,最小的六岁,最大的十五岁,有些带着助听器,有些完全听不见声音。
程远站在前面,手有点抖。他拿起一支蓝色蜡笔,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,然后停下。
“这不是太阳。”他说,声音不大,但通过手语老师翻译后传遍教室,“这是我昨天做噩梦时的心跳。它很大,很重,压得我喘不过气。”
孩子们静静地看着。
他又画了一个歪斜的三角形。“这是我在医院醒来看见的天花板裂缝。我一直数它有多少条分支,因为只要还在数,就说明我还活着。”
一个八岁的女孩突然举手,接过纸笔,飞快地画了一团黑色的毛线球,中间扎着一把剪刀。她指着自己胸口,又指指门外的湖,做出投掷的动作。
手语老师解释:“她说,她的难过像一团乱麻,但她不敢剪开,怕里面藏着妈妈的声音。”
教室里一片安静。程远走过去,蹲在她面前,轻轻握住她的手,然后在她画的毛线球旁边,添了一只正在梳理线团的手。
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慢慢解开。”他说。
那天结束时,每个孩子都留下了一幅“情绪图谱”。有人画了暴雨中的树屋,有人画了锁住嘴巴的铁链,还有一个男孩画了自己站在山顶,脚下是万丈深渊,但他手里握着一根细细的风筝线。
程远把这些画带回房间,整晚没睡。第二天清晨,他在低语室录下第三段音频:
>“我不知道能不能当一个好老师。
>但我终于明白,有些课不是我去教别人,
>而是他们教会我,
>如何用另一种方式活下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