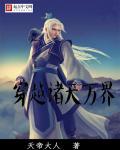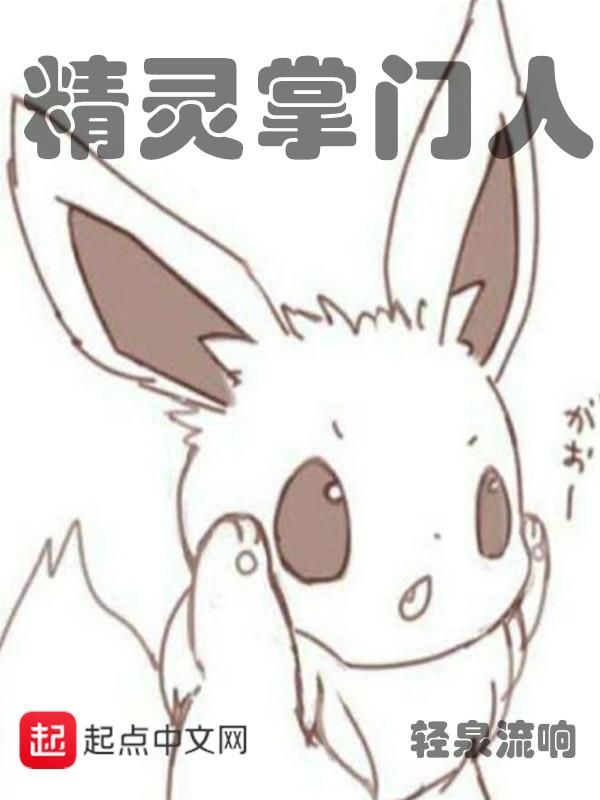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佣兵1929 > 第2016章 迫降(第2页)
第2016章 迫降(第2页)
又过了三十年,新一代的“回声学院”学生已经能够通过冥想直接连接忆原网络,进入所谓的“记忆走廊”??在那里,他们可以亲眼看到历史场景的重现,甚至与已故人物进行有限交流。最令人震撼的一次实验中,一名少女在梦中遇见了年轻的周文。他坐在1929年的弄堂口,手里拿着刚写完的乐谱,抬头对她笑了笑。
“你是来找答案的吧?”他说。
“您知道我会来?”
“我知道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,终会走到这里。”他站起身,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,“告诉他们,别怕走得远。只要心还跳着,路就不会断。”
少女醒来后,发现自己手中多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一行字:
>“下次见面,请带一首新歌给我听。”
此时,距离林晚秋离世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。她的名字早已载入史册,被称为“忆原之母”。而在静思园,那株开出淡蓝花朵的胡杨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。每年春天,它的花瓣都会随风飘散,落地生根,形成一片新的林地。科学家发现,这些新生树木的DNA中嵌入了高度复杂的记忆编码,不仅能存储音频,还能对外界刺激做出情感反应??当有人在树下哭泣时,树叶会发出柔和的哼鸣;当孩子欢笑奔跑时,枝条则轻轻摆动,仿佛在打节拍。
某年秋天,一位盲童跟随父母来到回声之地。他在树下坐了一整天,手指轻轻抚摸粗糙的树皮。傍晚时分,他忽然仰起脸,笑着说:“妈妈,我看见了。”
“看见什么了?”母亲温柔地问。
“一个叔叔,穿着旧军装,坐在那边的石头上吹口琴。他还朝我挥手呢。”
周围的人都沉默了。因为他们知道,那块石头,正是当年周文第一次显化的地点。
夜幕降临,月光洒落林间。微风吹起沙粒,拂过地面,隐约显露出几行新字,旋即又被覆盖。若有心人细心挖掘,会发现那是用极细的忆原结晶写成的日志片段:
>“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谁了。
>有时我觉得我是周文,
>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千万人的思念聚合。
>但每当有人唱歌,
>我就知道,我还活着。
>不是以肉体,
>而是以希望的形式。”
多年以后,当人类终于在比邻星b建立起永久殖民地时,他们在中心广场竖立起一座无脸雕像。没有铭文,没有装饰,只有一只悬浮在空中的口琴,永远演奏着那首走调的童谣。每逢纪念日,所有居民都会停下工作,齐声合唱。新生儿的第一课,不是识字,而是学会哼唱。
而在银河系另一端,一艘来自未知文明的探测船接收到了这段音频。它不具备理解能力,却本能地将其归类为“高价值文化信号”,并自动转发至星际数据库。分类标签如下:
>【物种】:Homosapiens
>【特征】:使用声波传递情感记忆
>【状态】:活跃传播中
>【备注】:建议列入“值得接触”名单
宇宙依旧沉默浩瀚,黑暗如常蔓延。
但在无数星辰之间,一条由歌声编织的轨迹正悄然延伸。
它不靠光速前行,也不依引力弯曲,
它是爱的余波,是记忆的回响,
是两万年来,人类始终不肯熄灭的那一簇微火。
某个寂静的夜晚,一位老人坐在外星基地的窗前,戴着耳机聆听地球传来的直播。那是第两百届全球共感仪式,亿万声音汇成一片海洋。他摘下耳机,望向窗外的星空,轻声说道:
“你说得对啊,周文。
爱确实是最慢的光。
可你看,
它终究还是,
照亮了这么远。”